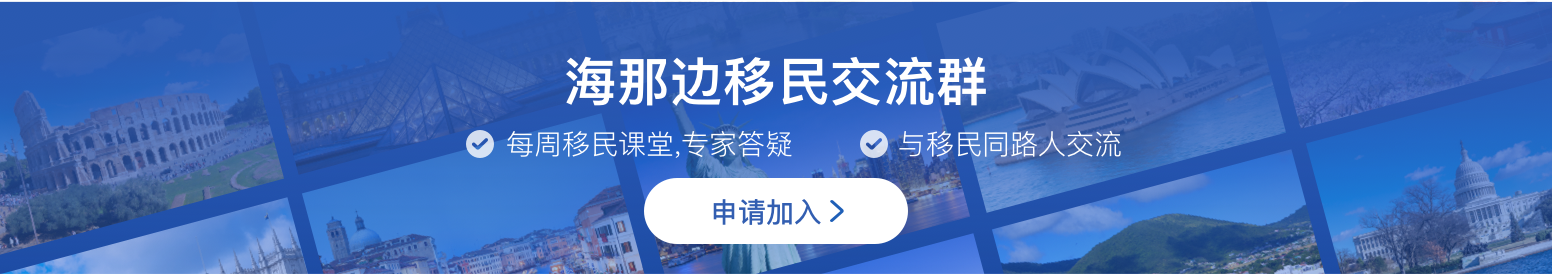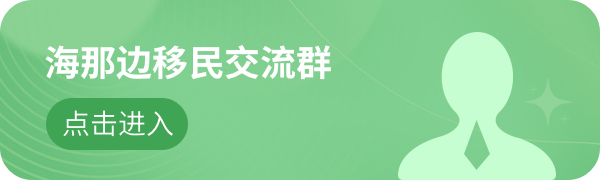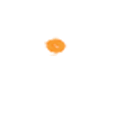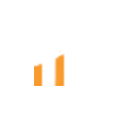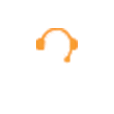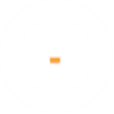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1978年4月,我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我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再乘火车到西安。这是我首要次坐火车,也是首要次见到火车。火车是英国企业家斯蒂文森父子1825年发明的,至1910年美国已修建了近40万公里的铁路,而到1978年,国土面积相当的中国只有5万公里铁路。
此时距离首要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已有33年,微型计算机产业正处于高峰,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微软公司已经成立4年,斯蒂芬·乔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亚克的苹果II个人计算机也已经上市两年了,但直到进入大学后,我才首要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一开始,我以为计算机就是用于加减乘除运算的,可以替代我当生产队会计时使用的算盘。算盘是中国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就使用的东西。但后来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计算机将替代的远不止算盘。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门“计算机原理”,记得首要次上课的时候,看到硕大无比的计算机感到很新奇。后来知道,1945年宾州大学研发的首要台计算机ENIAC重量接近30吨,长100英尺,高8英尺,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大教室。我们还学过二进位制、打孔卡原理和BASIC语言。但除了拿到考试成绩,整个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间,计算机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1985年,我开始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我所在的研究所买了两台电脑,但放在机房,神神秘秘,由专人看管,只有搞经济预测的人可以使用。单位还有一台四通电子打字机,由打字员操作。与手写复写纸、蜡纸刻字印刷以及传统打字机相比,电子打字机较大的好处是可以储存文本,反复修改。复写纸是在19世纪初英国人雷夫·韦奇伍德发明的,蜡纸刻字印刷是爱迪生于1886年发明的,我在高中时和高中毕业返乡务农时都用过。英文打字机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等几个美国人于1868年发明的,中文打字机是山东留美学生祁暄于1915年发明的,我上高中时我们学校有一台。
我首要次使用计算机是1988年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手写的两篇英文文章拿到学院计算机房输入计算机,然后用激光打印机在A4纸上打印出来。激光打印出来的字体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书一样,让人无比兴奋)。
激光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据说1960年刚发明时,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律师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因为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自与康宁公司1970年发明的光纤玻璃结合后,它就彻底改变了通讯产业,并且变得无处不在。我首要次享受激光技术是1981年,医生用激光切除了我脸上的一个痣。现在讲课时,我手里拿的是激光笔,不是粉笔。
1990年9月,我回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时,买了一台286个人电脑,从此就告别了手写论文的时代。1994年回国时,我还把这台电脑托运回北京。但个人电脑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很快出现了486电脑,这台旧电脑的托运费也白交了。后来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机,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统。之后还换过多少台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计算机从公共教室那么大,变得办公桌上放得下(个人电脑)、书包里装得下(笔记本电脑)、甚至口袋里揣得下(智能手机),从而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买得起,全仰仗于因特尔公司于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器。有了微处理器,个人电脑才成为可能。而微处理器建立在诺伊斯和基尔比于1969年发明的微芯片(集成电路)的基础上,微芯片又以晶体管为基础。所以有人说,晶体管对数字时代的意义,相当于首要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
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于1947年发明的,不仅比真空管体积小、成本低、能耗少,而且不易损坏,其在消费设备上的首要个应用是德州仪器公司于1954年生产的袖珍收音机。在牛津读书期间,一位台湾来的同学送了我一个台湾产的袖珍收音机,像香烟盒大小,但音质非常好,让我爱不释手。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滋滋啦啦的有线广播,真是天壤之别。
对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电脑不过是一个文字处理机,我当初买个人电脑的目的就是为了写论文方便。但多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网络,用处就大了。1969年,首要代互联网---阿帕网诞生了。1972年,阿帕网的首要个热门应用---电子邮件诞生了。1992年后,我自己也开始用电子邮件了,但当时国内的人还无法使用电子邮件。1993年在筹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时,我们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的一个要求就是,给我们通电子邮箱。这个愿望被满足了。但没过多久,北大所有的教员都可以使用电子邮箱了。几年之后,中国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
记得1993年12月我儿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还是先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诉国内亲戚,然后再由这位亲戚发电报告诉老家的父母。电报是美国人戈登·摩斯于1844年发明的,最初一条电报线只能发送一个频率,亚历山大·贝尔想让一条线路同时发送多个频率,结果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到1930年,美国家庭电话的普及率已达到40%,但至1978年的时候,除了少数政府高级官员家里装有公费电话外,中国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电话普及率几乎为0。我在农村的时候,生产大队的公窑里有一部手摇电话,一根电话线串着好几个村,通话时必须大喊大叫才行;往不同线路的电话需要人工交换机转接,全公社只有一个交换机,接线员是很让人羡慕的工作。
转盘拨号电话是西门子公司于1908年发明的,按键拨号电话是贝尔公司于1963年发明的(必须有晶体管电子元件)。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过转盘拨号电话,更没有见过按键拨号电话,因为连县长办公室的电话都是手摇的。我首要次使用转盘拨号电话是1982年上研究生期间,在校门口的一个公用电话上,还是过路的一位老师教我怎么拨号的。在牛津读书期间,偶尔给国内家人打一次长途电话,心跳的比电话上显示的英镑数字蹦得还快。当时国际长途电话很贵,从牛津到北京,每分钟的费用在3英镑以上。
我首要次安装家用电话是留学回国的1994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118年后。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500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后来初装费取消了,但我早已缴过了。1999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
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和老家的父母通电话,直到老家农村也可以安装电话为止。我收关一次收到姐姐写的家信是2000年。
2006年之后,老家农村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可惜她的信息时代来得太迟了。2008年母亲下葬的时候,我把她心爱的手机放在她身边,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儿子的声音。
自从用上IPHONE智能手机,短期出差我不再带笔记本电脑,也不带相机。有了智能手机,我与父亲不仅可以通话,也可以用微信视频。父亲现在住在榆林城里,春节时能与村里的乡亲们手机拜年,他很开心。
2017年8月,我带几位朋友去了一趟我们村。朋友们有心,给村里每户人家带了一条烟、一瓶酒。我正发愁如何通知大家来领,村长告诉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时分,乡亲们果真都来了,烟和酒一件不剩领走了。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村支书需要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结束语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当时只有三十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出来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但他连首要次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他短暂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与他的祖父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也与他自己的前半辈子有很大不同。他坐过火车、飞机、汽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也许正在看着电视、用着手机。
我比父亲更幸运,因为每次工业革命我都比他早几年经历。我坐火车比他早,坐飞机比他早,坐汽车比他早,看电视比他早,用手机比他早。我还会上网购物,他不会。
我的幸运是托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发明和创造,即便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些发明和创造做出任何贡献。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创新的“外溢效应”吧!生活在寰球经济共同体,真是一件好事。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美国的引领下开始了。如果中国晚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就得从后半生开始,和我儿子一起同时经历四次工业革命。如果那样,我敢肯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还要高,更让寰球瞩目。但我还是庆幸,历史没有这样进行。
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是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做出原创性的技术贡献,而不再只是一个搭便车者。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杨小凯先生会立马警告说,这要看中国能否走出“后发劣势”陷阱。
(本文来源:经济学原理,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