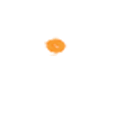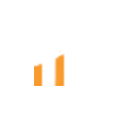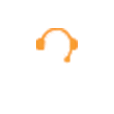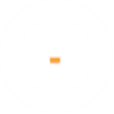11月1日,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张宏江博士与图灵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教授 John Hopcroft就“人工智能:战略、研究与教育”进行了一场对话。
计算机科学是当下的热门专业,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历史不过60多年。作为计算机科学的先驱人物,John Hopcroft见证了这门学科的建立、成长与繁荣。
1987年,康奈尔大学教授 Hopcroft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Robert Tarjan因为在“算法设计、分析以及数据结构方面根本性的贡献” 荣获了计算领域的较高奖图灵奖。
今年80岁的Hopcroft,不仅学术上成就卓越,在教书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也堪称楷模。早在数年前,他就来中国,出谋划策,身体力行,帮助中国提升教育的水平。2016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2019年11月1日,智源研究院理事长张宏江博士与Hopcroft就“人工智能:战略、研究与教育”进行了讨论。在40分钟的谈话中,Hopcroft分享了对人工智能、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刻看法。
《知识分子》整理节选了两人的谈话,以及Hopcroft的个人小传,以飨读者。
01.大学真正的使命是产出下一代的人才
张宏江:你在1986年获得了图灵奖,在座的观众很多人那时候还没出生,请你谈下当时的情形?
John Hopcroft:那个年代,早期的计算机科学非常简单。那时,要决定一个算法是不是行,就把它在电脑里跑一遍,测一下解某个问题花费的时间,这时如果有另外做这个问题的研究者,提出另一个算法解这个问题,花的时间更少,但其实是不知道总归为什么(花的时间少)。第二位研究者用的数据和首要位一样,但如果换做用某种随机的数据,实际上却算的更慢。
我觉得我们得用数学的方法来决定一个算法会更慢的原因。我提出最坏情形的渐近分析方法,然后我发展了一些技术,比如分而治之,来开发这种形式的优良算法。这么做了以后,就将之前算法的那种教授方式转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
张宏江:真好。你在普林斯顿教计算机科学时,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你从哪找教学的资料?
John Hopcroft:我想我应该提一下,我获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时,并没有计算机科学专业,我的学位是电子工程,我也是受聘于普林斯顿的电子工程系,但我倾向喜欢电子工程的计算机学科的那一面,我更喜欢数学一点。那时有少数几篇文章,我就是这些文章基础上开发了这门课,之后这门课被其他大学广泛地采用,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理论课。
1967年我到刚成立的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开始在与我志趣更贴合的系里发展我的职业,这也是更好的选择,我也就有这样的机会帮助建立一所寰球当先的计算机科学系。
张宏江:对深度学习,你怎么看?
John Hopcroft:人工智能像是某种工具箱,里面有各种工具,而深度学习是这些工具中的重要的一种,至少在今天是这样。
不过,某种程度上,深度学习只是高维空间里的模式识别。比如,你训练了神经网络来进行图片分类,给一张特别像自行车,但却不能骑(没有自行车的功能)的照片,模型依然会认为是辆自行车。
实际上,我不认为这是种智能,因为在图片分类中,并不能从图中的物体里提取出功能,我想还得等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一点。当我们真的理解了功能,我们才会进入到或许是接下来的信息革命。
张宏江:从算法的角度,你怎么看,是数据和参数的问题么?
John Hopcroft:或许我能谈一下我是如何看待做研究的。寰球上有两种研究,一种是基础研究,一种是应用研究。我看到的人工智能目前的状态是应用研究:我们开发技术用到解决重要的问题中去,很成功,对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很重要,但基础的研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做基础研究单纯是因为研究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就是这样简单。在美国,大学里是不做应用研究的,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致力于基础研究。或许我该换个词,不用使命。大学真正的使命是产出下一代的人才。
当我们雇佣教员的时候,他们有40年的职业生涯,我们想雇佣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能保持活力的教员。我们喜欢的一点是,是有好奇心。我们雇佣某个人,我希望,不是看他们正做什么研究,而是看他是不是对此感兴趣,而且愿意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活跃。
你或许说,美国这不是在盲目地资助大学的基础研究吗,没啥目标?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好的投资,但实际上,这可能是美国做出的很好的投资。因为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方向探索,很多人没产生什么影响,但有时有些人做了一些事就创造出了整个全新的产业,创造出几十亿的工作,几十亿的金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投资,希望能坚持这一点。
02.对人工智能进行长期的投资
张宏江:深度学习还会有进展么?
John Hopcroft:这些年来,深度学习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棘手的是我们尚不能解释这背后的原因。如此一来,如果你是一名教员,那么教课时你便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你现在教给学生的是一门实验学科,迫切需要发展出能够解释深度学习的理论,为什么有用。
一个困难是,以模式识别为例,假如你有一个猫的系列或者一个狗的系列,你没有一个关于这个系列的数学定义,那或许就有研究者退一步,造出一个数学上定义清楚的类别,能帮助证明深度学习有关的定理。我之所以关心理论的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让教课变的更加容易。
张宏江:你怎么看无监督学习?
John Hopcroft:要弄清如何做无监督学习,或者如何从一张图里面学习很重要。我可以讲一个之前和我的三岁女儿的故事,我有一本看图识字的书,我曾和她坐在沙发上一起看图然后认出是什么。有一次我和她走在街上,她指着说,爸爸,消防车!她实际上只看过一次消防车的图,就认出来了。
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或许人学到了如何去学。她在看那一张图之前已经看了几百万张图,之后她从一张图中学会了如何去学。这意味着,关照多个学科是重要的,比如理解人脑是如何工作的,在过去的25年有很多的关于人脑的研究,也许知道人脑如何学习会帮助到机器如何学习。
张宏江:了解到人脑是如何工作后,可以将其转化成数学模型或者算法么?
John Hopcroft:我对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知道的很少,我读过一些研究,好像刚开始的时候脑中的神经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然后有一个转换阶段,神经元靠的近了。另一件事是,在大脑的前5年,神经会产生新的连接,然后有一个转换期,再有新的神经连接也不会有太大用处。你可以借鉴这些,然后看是不是可以用来训练神经网络。
基础研究有一个特点,好几千人尝试各种的想法,但往往没什么价值,但有一两个人会有非常重要的回报。
张宏江:总归是哪一两个人?
John Hopcroft:这个事先是不知道的。我可以稍微谈一下美国的资助。当我提交申请书时,资助机构并不要求我按照申请书所写的来进行研究,他们之所以进行资助,是想产生下一代的人才。如果我觉得另外的研究是重要的,他们是高兴的。这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我完成研究项目时,我不会写汇报,而是大学会写汇报,说明钱是怎么花的。资助机构也不指定哪些方向会得到回报,他们评判是根据下一代的人才,他们开拓了哪些方向。
张宏江:我很好奇,如果你是资金管理者,会把钱投入人工智能的哪个方向上?
John Hopcroft:要决定方向的话,我觉得有两件事是值得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是短期的,你想提高中国或者北京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创造就业,这样下来你或许得帮助公司所做的事,比如人脸识别、图片识别、机器翻译,所有这些重要的事情。但你还得或许花点钱,用来产出下一代的人才,还应该着眼于长期。
张宏江:现在几乎每个主要国家都有自己的AI战略,你认为近些年两届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做对了什么?
John Hopcroft:或许我应该说一下,在我开始职业生涯时,政府甚至不相信计算机科学是重要的。政府寻求一些物理学家的意见,他们倾向于认为计算机科学是在训练程序。
现在看来,一个新的领域要发展是很难的。老的领域不想让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但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里面提高了计算机科学的资助金额,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也进行了很重要的资助。
但至于你说的AI战略,从美国的版本来看,都是些很明显的东西,如果你问非科学家该怎么办,就是对人工智能进行长期的投资。我读过后,没有从中发现什么有洞见的的策略。
张宏江:美国会在人工智能上一直领先么?
John Hopcroft:我也不确定美国是否能够在人工智能上保持领先,因为我觉得投资还不够。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进入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社会的性质将随之改变。
我想说,学生往往都会用脚投票,学生意识到将来是信息技术的时代。我相信今天的大多数美国大学,有10%的专业是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但经费并没有按照这一趋势进行分配。
张宏江:你怎么看待中美人工智能的发展?
John Hopcroft:在这方面,中国其实有很多优势。以手机为例,当移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美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已经安装了有线宽带,所以我们并没能足够重视它,中国则投入大量资源对这一产业进行发展,因此比美国在很多方面领先,比如中国人用手机做几乎是所有的事情,美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我想在一些地方,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完善的设施,发展的速率要快很多。
张宏江:自动驾驶面临一些安全的问题,但也有人担心工作被代替,你怎么看?
John Hopcroft:要在城市的街道上驾驶是非常难的,有行人,有自行车,有汽车。但美国有洲际高速路,车就在车道里开,不会来回变道,自动驾驶的话就要容易些。我想象的,司机把车开到高速路口,然后车辆自动驾驶,出高速时再由司机来接管。这个问题就要简单的多。
张宏江:我也同意,自动驾驶卡车要容易,但为什么没怎么做?
John Hopcroft:我不知道答案,或许是因为相对于在城市载客,可能没有多少“钱”景。
在自动驾驶上,车路协同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或许可以让道路将信号传递给车辆,再由车辆传递给彼此,把路封起来,不要让动物穿行等等来实施。可我们似乎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试图去解决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般性的问题(让车辆自主自动驾驶)。中国可以很容易地由政府设置一条“自动驾驶专用车道”来进行试验,但在美国就几乎不可能。
张宏江:现在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中国,很多大学都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你的意见是?
John Hopcroft: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创立这么多的人工智能学院,但也可能是政府限制计算机科学相关的专业,但太多学生想学这个,所以大学就建立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等专业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大学会想建立一个信息科学这样的系,像之前的工科、科学、艺术一样。因为这个领域的专业太大了,需要5、6 个系,或许信息科学学院可以把这些都囊括进来。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科,我想很多学校做的是对的事情。
张宏江:但人工智能也有起起伏伏,如果这次人工智能的冬天来了,那这些学校再裁减人工智能的专业么?
John Hopcroft:当情况变的时候,事情也会随时有变化。
以我曾学习研究的电气工程为例,它曾经是一门关于发电和能源传输的学问,但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将无线电和计算机也融入其中,电气工程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们不断的变化,人工智能也需要如此去做,如果人工智能做的还和我们今天一样,那可能会有问题。
我就是相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是很关键的社会,工业革命解放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自动化智能,我不认为这个进程会停下来。
03.研究发表量多正在伤害科学
张宏江:除了图灵奖,你还有一个重要的荣誉就是“中国政府友谊奖”。你也曾经在教育方面给我们的总理提出过建议,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这么做?
John Hopcroft:一直以来,我都想做一些能够让寰球更好,让尽可能多人受益的工作。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在15个不同国家(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印度等)都曾进行过教育工作,帮助过几个教员和学生,但从未有过机会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教育系统。
中国教育部邀请我到中国,就跟之前这些国家有很基本的不同,政府希望对本科教学教育进行提升,我也就有机会会产生影响。
其他国家的政府集中在其他事情上,努力提高教育不是他们最关心的,我觉得以前这些国家的优势是能源和材料资源,但这些别的国家也有,知名国家有的是人才,这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动力。
中国,我想是知道这点的,如果你和中国政府谈,他们会说,我们必须提高本科生的教育,提升人才,这样公司才能不断扩张,持续的盈利。这是中国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张宏江:你对高等教育有什么建议?
John Hopcroft:我应该提一下,20年前,孩子必须有个学位才能得到一份工作,上大学的人数以每年100万的数量增长,中国要持续发展,必须有能力容纳更多的学生,相当于每年要新建50所大学。
在有能力收纳这些学生之后,还要提高学生的质量。
我觉得,其中的一个障碍是,在中国,一个校长的任期只有五年左右,因为他们是政府公务员,任期结束后会转到另外一个工作。为了证明他们的成绩,他要盯着大学国际排名这个指标。
然而,这些排名考量指标是基于研究,发表文章的数量,而和大学的宗旨,也就是造就下一代的人才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对于高校校长的评价维度。
我交谈过的校长都是寰球水准的人,有知识,有才能,如果把本科生教育作为评价他们工作好坏的指标就好了。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觉得中国知名学校的一年级学生质量比美国的大学好,如果清华、北大和上海交大等能提升本科教育,那就可以超过斯坦福、伯克利和MIT这些机构。
张宏江:你对教育有非常大的热情,为什么?
John Hopcroft:我非常享受教育和科研,或许我可以给新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如果你想在职业上成功,你一定要做你喜欢的;如果你是教学生,不要仅仅教他们教室里学的,还有其他的技能。狭隘的技术教育可以带给他们首要份的工作,但你应该给予他们更宽广的教育,历史学,社会学等,促使他们成功并享受人生。
张宏江:作为年轻的教员,如何在发表文章和教育之间得到平衡?
John Hopcroft:如果一个本科生找到我,说希望能够做些研究,我会劝告他,科研可能不是你现阶段最应该花时间的事情,除非你想要借此进入一个博士项目。因为如果你要进入一个好的博士项目,或许你得有发表。
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在我没发过一篇论文的情况下雇佣了我,今天我怕是连研究生都进不去。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我是否在整个职业生涯长期保持活跃,而非我已经做了的研究。
张宏江:在计算机领域,我们很多人都是先成为IEEE Fellow,之后继续做的好,成为ACM Fellow,可你却是先获得图灵奖,然后才有其他的荣誉和头衔,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给年轻人?
John Hopcroft:完成要求你的较低论文发表量,然后把精力尽可能投入到那些基本的研究上去。如果你做出了基本的发现,那你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
事实上,我认为今天寰球上如此之高的研究发表量正在伤害科学的发展,如果你学一门新的学科,有太多的文章要读,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筛选、检索的时间。
(未完待续)